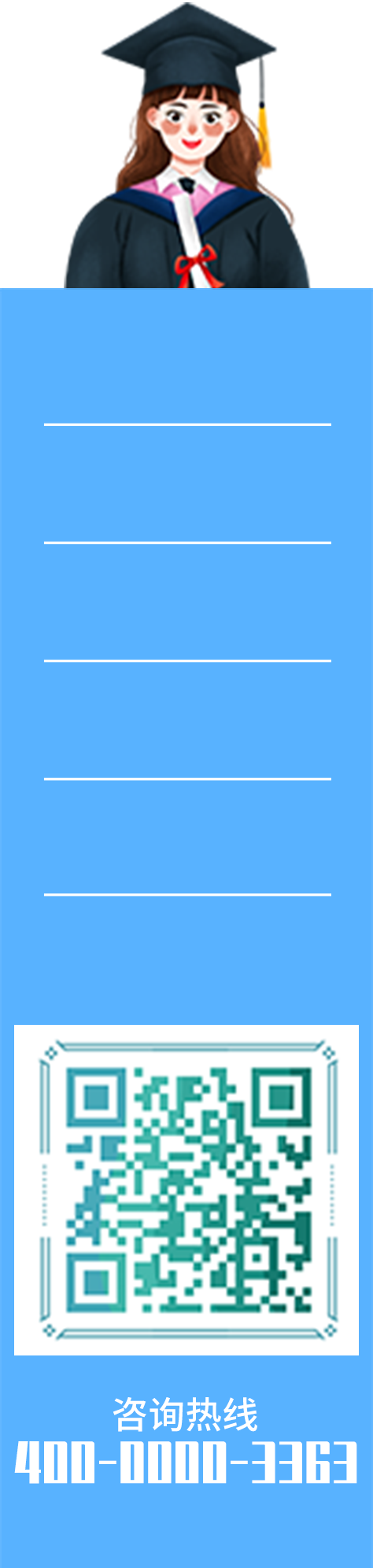一、成长与变故
“人就是向死而生”,从蒙田到海德格尔,都说过类似的话,据说这就是哲学之所以诞生和存在的原因之一,参悟透了这种究极的问题的人,多少也就触摸到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可是,当我在课堂上和蒙田的随笔录中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无法明白,“向死而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直到我从一个懵懂少年,经历了祖父的死------一场影响至今的变故。
小时候父母整天都得下地干活,祖母在家烧火做饭家务繁多,于是在公社面坊工作的爷爷就把我背在背上,一边干活一边带我。农村的生活虽然清苦、受限(贫穷就是一种限制),但远僻的山村与世无争,总体上人们过得自足、平实而快乐。即使到 2000年9月家里凑钱、亲戚出路费让我走出了18年来都不曾跨出的河边山村,远赴到两千多里外的津门求学的时候,我仍是一个没有什么“见识”,不曾体会过什么复杂、矛盾纠集的、令人内心不安灵魂震颤的东西的童蒙少年。
为求学离家15年来,“回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奢侈的概念。在我12岁刚刚小学毕业之后,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另一个县一所更好的中学读书,我寄宿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在家里待的时间很少。学校在长江北岸,家在长江另一边,回家一趟很远:坐火车,根据不同的季节在河边找寻渡船不同的停靠地点,过了河之后再翻山越岭一个钟头才能到家。。蜀道难,山高路不通,每次回家无论是雨后泥泞还是烈日当空,都是背着沉沉的箱子爬山-------倒是实践了前人所谓“野蛮其身体,强健其精神”之训。在我的高中时代,一年之中更是十有八九的光景是不在家的。记得当时同级的(2000届)学生竟有约千人,分布在十几个班级里。竞争激烈,脑中只有奋力前进考好名次。高一的时候,外婆去世了,家里不知为何有“噩耗不传读书郎”之习俗,葬礼背着我做了;我爷爷奶奶七十岁大寿的日子,我也没有去见一见他们。寄人篱下六年之后,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南开大学哲学系),我去到更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地方读书。
因为没有见过危险,所以便认为世界不会有危险——这是一种多么鸵鸟又多么一贯的童真心态啊!所谓幼稚,就是不晓得变故;所谓成长,就是接受了变故;因为没有见过危险,所以便认为世界不会有危险;因为从未经历过什么不美好,便总是以为生活永远都会美好地平静下去。如果不是大二期末那场变故,也许我会一辈子在这种素朴的生活理念中,恬淡自足地走着自己的人生路。
就在我读大学的那两年,爷爷不知何时患上了“肺心病”。等我 02年回去的时候,爷爷已经脸色憔悴,元气大失了。记得三十前两天,我陪爷爷去看医生,医生只给抓了2天的药,说:“初一不要吃,大年初一是不兴吃药的”,我居然也没有意识到,那里面已经包含着医生的某种勉强之词。陪爷爷走在回家的路上,爷爷慢慢地走在一条又一条高高低低、清清冷冷的田坎上,我居然不怎么忧虑(!)-------想来,我上大学后的第二个春节时,爷爷已经走到了生命最后的百分之五阶段了。为何我竟然毫无察觉只以为是普通的年老疾病?是我没有能力察觉还是我的软弱、天真、幼稚让我盲目?
大二期末考试的前夕,怕影响我的考试成绩而照例对我采取隐瞒态度的父母,并没有告诉我爷爷撒手人寰的噩耗。然而这种刻意为之的隐瞒,最终又正是由我自己去亲手察觉和拆穿的。在天津一个六级大风狂刮的夜,我手握着三天前上自习时给爷爷写好、但却不知为何尚未寄出的一封信,想向家里问问爷爷的情况。家里没有安电话,我打到了邻居家里;等了许久,电话那头父亲刚一开口,沙哑哽咽的嗓音便暴露了一切:爷爷已然不在这个人世三天了!
令我灵魂出窍的是,他撒手人寰的当日,正是我写信的那天(02年7月6号)!
突如其来的变故,把 “死”这个讯息强行塞入我的脑海。看着沧桑、年进半百却又像孩子一样哭泣的父亲那种(对考试中的我)刻意隐瞒、却又下意识希望内心的悲痛得到发泄的心情,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断电话的。那现身出来的“死”是一种巨大的、无边的空白-----这空白是对脑和感官、心和身那本然亲密联系猛然中断后的不适应,是对“事情结局”之永不可逆、“生”之永不可得的恐惧体验,是对人生中(果真)有黑洞一般、像无底深渊那样虚无感的巨大惊慌!“死”、人生在世的有限性或者叫“变故”,总是由不得你准备与否,由不得你喜欢与否便降临了。
如果说生命是一张叶子,当年轻一代尚未抽芽长绿的时候,年老的一辈就已经退出生命舞台了-----生活的冷酷对我而言,莫过于如此。
人的脆弱性、生命的不可留,让我猛醒;人生的有限性爆发了我对生命自由的强烈渴求。得知噩耗过后的暑假,跟每年一样,我住在学校,做家教没有回家。我的精神突然变得蛮野起来,开始敢于去开拓之前因为安逸平稳的生活而不敢去开拓的那些可能性。比如,去脚踏一个巨大的、陌生的、我一向惶恐不安的平原城市,去打工;打破人与人之间强大的习惯思维的约束,去认识所有值得交流的人;无论场面多么宏大的讲座,尽管我只是一个学术道路上稚嫩不已的黄毛丫头,但只要我从讲座中有共鸣或者疑惑和不解,我就敢于站起来和讲座者表达我的观点(我很珍惜在南开的四年各种哲学讲座中,我和叶朗先生、杨大椿先生、霍桂桓先生;和已故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先生的思想问答)。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成长就是开始知道并处理生命中的变化。可是人对水土、气候的改变容易适应,而文化、习俗、个性的变化不容易做到。最难“消化”的是观念上的异质------所谓“精神上的打击”,其本质都是在观念层次根深蒂固接受不了异质物。习惯了单纯、美好、完整的家庭模式的我,无法接受“不完整”的概念。02年后,虽然我的性格变得多了很多阳刚(变得积极、乃至亢进了),但内心深处,却仍然难以平息对生死之转变的困惑。而在爷爷去世后五年,一年半前,我深深眷恋、爱着的奶奶也离我而去了。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在记忆中重温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的时光,看着他们在我的记忆力微笑。想着他们,想让时间定格,唯独不想接受“现实”。
也许是爷爷的死----第一个至亲离开------的时候,我的父母没在身边安慰和引导,我一直都学不会如何承认死亡;在六年来,自己多次有过一些极端的念头,这些念头(逃避现实的挫折、活着没意思,)让我惊讶、羞耻和痛苦,因为这和我自我认同不符:曾几何时,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哲学史上在活力十足的八月出生的哲学家 一样,是一个充满蛮野力量、充满向上阳光、侠客一般温暖慷慨、对哲学有自己的领悟力和禀赋的人。自我认同上的矛盾冲突是最让人痛苦,却也最让人警醒的。我意识到,六年来,原来我都不曾真正地消化掉“死亡”所代表的人生的虚无,事实上六年来我一直被一种虚无主义的想法困制:既然反正一切都将是要失去的,不仅爷爷,奶奶,即使我的父母双亲最终都将放开那携持着我的手,而将我一个人留在人生之路上,那我还保留着感情、信仰和憧憬做什么?
虚无主义、悲观主义这个毒素长久寄生在我身上而我不自知。
尽管我一度自我认同自己为一个乐天派,一个在自己的朋友遇到任何程度的失败挫折时都会不遗余力、一如既往地相信他、鼓励他的人,一个在朋友眼中像阳光一样温暖和侠客一样慷慨的人!但随着环境、人事、物事的改变,每当我情绪陷入低谷时虚无的毒素就爆发,(从2002年至今)我曾经有过大约十几次轻生的念头。尽管只是念头,但每一次发生时的痛苦,都是实实在在的;那种内心沉落的感觉,即使想想,也让我不寒而栗。人在这世界上最不愿意重复的,大概就是重复的失望了。
虚无
当我在异乡求学的过程中遭遇那些失败挫折而痛苦、动摇、想放弃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死”其实就是虚无主义的别名。
之所以可能(竟然)产生轻生、放弃的念头,是因为我内心存在没有清楚出去的虚无感。这个虚无感内在的来源就是爷爷的去世。自爷爷、奶奶去世,我就一直没有学会把“死”和虚无主义分开。当我允许自己保留对痛失亲人的悲伤和无奈时,不经意间我也没有阻止虚无主义的寄生------既然再美好的东西反正最终都要失去,为了寻求这些美好的东西而努力有什么用?!今天我明白不能再逃避了,必须将六年前的那次打击、那个心结做一个了结。生活中永远没有单面的东西:单纯片面的美好幸福是不可能的,而单纯片面的悲观绝望也是没有必要的。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得失、有无本来就是相生的,难易本来就是相成的,为何过去我只看一面?六年来我一直在亲人的死的阴影下生活-----也许这个时间对某些人来说看似长了一些(而对某些人来说,却还仿佛不够长)为何我要执着于一面、单单去在意那一面?
面对“虚无”和“生生”同在的人生事实,是直面还是继续逃避呢?-----“To be or not to be?” 莎翁这个台词之所以经典,就在于他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的是人人都可能遇到、人人都必须时刻深思的心灵难题。其实我明白,最终难题还是躲不过的,躲了六年又如何?我想要一个干脆的解决。
事实上,对死亡的解决很简单:我的生命力越壮实,爷爷的生命力也就得到了延续。因为他的血液继续在我身上流着啊!我的身体和灵魂,也有他的一部分啊! 当我用眼看世界的时候,难道我不是也在用他的眼在看吗?当我笔端文思泉涌,艰苦探索学术之路的时候,不正也是他的睿智在我身上的展现吗?当我站在山岳之颠,观天地大化流行而喜悦的时候,难道不正是他在我心中微笑吗?轻生,沮丧、绝望、堕落、自我放逐,这才是对他最大的不敬不尊重啊!我应该学会尊重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亿万年造化的奇迹,谁知到在这白驹过隙的人生百年间,蕴亿万年造化神秀、蕴几代人期待的某一个人,会创造什么炫彩奇迹呢?
二、因变而思、因痛而学
由真正经历生离死别多次,生活令那个在哲学课堂上被我们无数次讨论过、意向过却不曾体验过的东西“死”(亦即虚无)的观念,开始进入了我的意识中。
死,作为最明显的一种虚无,它无形无色、无边无际却又狠得,能让你的心像被挖出了一块似的;它像一个无形的罩子降落在你四周,又像一个从地底冒出的牢笼将你囚禁,在一种对生命和结局“不可逆”、不可续的体验中,它显示着它绝对的支配权!在接受死亡(不管是自己的死还是至亲好友的死)的时候,人类能做的,不过是无一例外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抵抗,消极,认同 。
生命脆如苇草,发生在我身上的,是对由死所引发的一系列虚无范畴的东西的剧烈困惑:亲情的不完整;社会中的不公正、不合理、不人道;理想的生命状态-----自由、幸福、按照自己的的天性来工作、拥有真正在一个层次上的能理解你的知心朋友等------的不在场,一个清醒独立的未来人生走向的不成形……整个大学本科四年,我都在对“哲学是什么”、“如何从事哲学”、等问题上苦苦追索,这种追索、思考贯穿了我的整个本科四年生活。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场合、任何一个可能的瞬间,我的领悟都会朝向这个问题上去。不知不觉中,我的思想进入一种根子上的静默中,我的人生中开始涌入思忖。面对生命个体如帕斯卡尔所说的苇草般有限和脆弱,我们还能做什么?我能反抗点什么?哲学能在这种对生命对自由、无限、美好、善的高呼呐喊中,做点什么?女性能学好或者适合学哲学吗?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哲学的形态、从事方式只有一种吗?!